萧红《呼兰河传》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异同,有没有像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记,林海印...
萧红《呼兰河传》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异同
有没有类似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记,林海印...鲁迅早晚拾起冰心的记忆,俞平伯《颜曹植》和朱自清《杂集》的背后,杨朔《李知弥与雪花张爱玲》的八卦,张謇《钟敬文西湖》的八卦,梁秋实《沈从文湖南之行》的雅屋小品,以及山里求人的生活~ ~我用我中国最美的散文集找了半天,选得很好。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写的课文,呼兰河传的作者是萧红写...
简化后,你会发现去掉“作者”或“书面”的正确答案是不合理的:城南旧事是林海印写的,《呼兰河传》是萧红写的。或者:城南的老故事是林海印写的,呼兰河的传记是萧红写的。
有没有像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记,林海印...
有没有类似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呼兰河传记,林海印...鲁迅早晚拾起冰心的记忆,俞平伯《颜曹植》和朱自清《杂集》的背后,杨朔《李知弥与雪花张爱玲》的八卦,张謇《钟敬文西湖》的八卦,梁秋实《沈从文湖南之行》的雅屋小品,以及山里求人的生活~ ~我用我中国最美的散文集找了半天,选得很好。

城南旧事是林海音写的课文,呼兰河传的作者是萧红写...
萧红《呼兰河传》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异同范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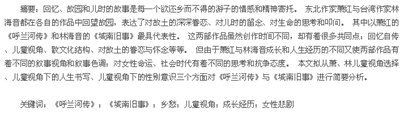
20世纪的中国一直受到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影响。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迅速引进,中国的经济形态、文化状况和作家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在创作中不断地回想起自己的家乡,他们的思乡之情也越来越强烈。小镇文学逐渐成为作家离开家乡的创作载体。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和师陀的《果园城》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在这种创作倾向下,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对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文学史增添了深刻的思考,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印的《城南旧事》。这两部作品是自传体记忆小说。儿童视角的书写使这两部作品具有散文化和怀旧美学的特征。然而,作为成人作家回忆过去的媒介,儿童视角背后最重要的是成人视角对某些概念和过去的思考和追求。同时,由于萧红和林海印不同的生活经历,这两部回顾性作品在基调、视角和思维上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拟从儿童视角的选择、儿童视角的生命书写、儿童视角的性别意识三个方面分析萧伯纳和林纾作品的异同,以及作者对生命和生活的思考。
儿童视角选择的背景
在记忆小说中,家和故乡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文化主导的国家。中国文化也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上。在这种文化的基础和传承上,中国人形成了强烈的家园意识和故乡情结。20世纪以来,小城镇文化和小城镇文学逐渐成为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对作者来说,他们在这里出生和长大,然后离开家乡,这在他们心中成为一幅美丽而不可磨灭的画面。对家乡的回忆成了他们流浪灵魂的慰藉。肖传国和林二的《呼兰河传》和《南城旧事》从作品的命名到内容的书写都洋溢着深深的乡愁。
(一)怀旧与童年情结
家乡生活和童年记忆总是密不可分的。童年是一个人生命的最初体验阶段,是记忆的起点,也是流亡者记忆中最难忘的部分。几乎每个离开家乡的人都有强烈的“童年情节”。当萧红和林海印回过头来看他们的家乡时,他们一定有童年的记忆。欣赏童年的快乐已经成为他们寻找精神安慰的一种方式。因此,对家乡过去和童年的记忆成为他喜欢在回忆作品中描述的重要部分,借用孩子的视角是再现过去的最佳方式。
小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镇。小红在那里长大,已经20岁了。呼兰河拥有萧红最受尊敬的祖父和最幸福的童年记忆。林海印,原籍台湾苗栗县,1918年出生于日本。他三岁时和父母回到台湾,五岁时和父母搬到北平。他在北平长大,结婚生子25年,1948年回到台湾。因此,可以说北平是林海印的故乡。“小镇生活已经成为作家童年生活中最深刻的精神镜像。小镇是作家童年的利基,最有可能成为他们的心理基础和人文背景。”
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后记中写道,“我写的不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因为它们充满了我童年的回忆,它们不能被忘记,它们很难忘记,它们写在这里”。《呼兰河传》的前两章描述了呼兰河人琐碎的生活和习俗。第三章是萧红和她祖父最幸福的后花园,这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有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和一个善良的祖父,那里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萧红写下这些话时,她脸上挂着温暖的图像和轻松、愉悦和由衷的微笑。
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经典代表,林海印的《城南旧事》以英子的眼光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北平南部的风景和人情,以及孩子们悲喜交加的离别,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充满北京气息的北京风俗画。小瑛子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她妈妈经常把“惠安会馆”称为“惠南会馆”,把“21”称为“两俗一记”;老北京的胡同、城南的游乐园、霍金和其他过去的习俗也清晰地出现在林海印的作品中。当提到写《北京南部的古老故事》的动机时,林海印说:“然而,我是多么想读到童年生活在北京南部的场景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这样真正的童年就会过去,心灵的童年会永远延续下去。《城南旧事》中的话是海印乡愁的最好释放。
(2)不同生活经历对萧伯纳和林二人创作动机的影响
在《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中,萧红和林海印都从儿童的角度表达了他们对家乡和童年的回忆。创作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儿童视角、分散的文化结构、回忆审美特征、自诉故事、强烈的乡愁等等。然而,萧伯纳和林二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也使他们在创作、表达和文本基调上有很大不同。
小红1911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市的一个地主家庭。在她童年时,她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漠不关心。除了祖父的关怀,小红感觉不到家的温暖。1929年后,她最爱她的祖父离开了,萧红失去了她唯一的爱。1931年,为了抵制家庭包办婚姻,小红逃离了家庭,踏上了漂泊一生的道路。从呼兰市到北平,从北平到哈尔滨到青岛到上海到东京,最后一位客人死于饱受战争蹂躏的香港。在此期间,他经历了流产、情感背叛、婚姻、贫困和长期痛苦,他的惨淡处境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因为萧红坎坷的经历,她的情感需求才比普通女性更强烈。正如萧红在《永远的愿景和追求》中所说:
“我会对这个‘温暖’和‘爱’的方面,有一个永久的愿景和追求”[4)。而这种追求恰恰是萧红不幸的原因,太多的爱太容易受伤。小红反对父母做媒,最初被家人视为一场大叛乱。在1935年8月创作和编辑的《东昌张氏族谱》中,她的父亲张廷驹和四叔张廷辉将萧红排除在家谱之外。1931年,“9·18”事件发生,东北三省沦为日本殖民地。从那以后,小红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如果一个人很穷,他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童年记忆中的呼兰市有一个最爱她的爷爷,一个美丽的后花园和萧红最温馨的回忆。
然后回过头来看她的家乡,用回忆温暖自己,从家乡和童年寻找温暖和快乐,这无疑成为萧红度过孤独、沮丧和凄凉的半辈子流浪的最佳方式。当她选择从孩子的角度回顾家庭和世界时,作品又有了强烈的客观性和经验。萧红写《呼兰河传》时非常孤独、空虚、没有安全感。记忆在某种程度上给她带来了平静,使她能够抵抗虚无的存在,并从巨大的痛苦中获得暂时的解脱。作者在寻求精神救赎和摆脱痛苦,所以他的作品中注定会有很多不太温暖和明亮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呼兰河传说》中总是有一种荒凉和感伤的气氛。
相比之下,林海印的童年和生活经历要快乐得多,也更舒适。林海印五岁时和父母去了北平。他的父亲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和谐的家庭。这个家庭经济繁荣,她的父母深爱着她。林海印在北平经历了童年和少年时代。1948年移居台湾前,他在北平结婚生子达25年之久。《城南旧事》写于1961年,当时林·海印已经40多岁了。中年人最有可能回忆起过去。千山满水,海峡互不分离,这不能阻止思乡之情的蔓延。对于已经在大陆生活了25年的林海印来说,虽然她的祖籍是台湾,但她小时候在北平南部的旧事和长大后在北平的生活都不是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她似乎再也不会回来了。林·海印从孩子的角度反思和回忆过去,但事实上她表达了自己的怀旧之情。在她的作品中,对城市南部的风土人情的描述,以及对她周围的人和事的记忆,更多的是因为失去了与祖国的联系而失去了无根的文化。
第二,儿童视角下的生活写作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儒家推崇的“君、君、臣、臣、父、子、子”的社会道德体系逐渐瓦解。儿童在人类成长阶段独立生活的意义和妇女解放运动共同构成了五四“人类发现”的重要内容。随着“以儿童为导向”的现代概念的提出,儿童的独立性在空之前得到了尊重。
对文学的影响是,儿童有限叙事视角的出现逐渐打破了传统的全知叙事视角,促进了文学叙事的变革。从鲁迅的怀旧、凌叔华的凤凰、萧红的呼兰河传记、林海印的《城南旧事》、迟子建的《北极村童话》和莫言的《透明萝卜》看,儿童视角极大地促进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发展。所谓儿童视角主要是指“小说借助儿童的眼睛或语调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特征。小说的叙事基调、姿态、结构和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选择的儿童叙事视角。
布思(W C Booth)曾在《小说修辞》中说过,就小说的性质而言,它是作家创造的产品。纯粹的不干涉只是一种奢望,这是不可能的。《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一直被视为儿童视角叙事的典范。然而,我们不能否认,作为一部回顾性小说,回忆是小说叙事的起点和动力。即使采用儿童视角来叙述作为成人作家的童年回忆小说,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整个文本总是有成人视角的声音,无论是隐藏的还是现在的。记忆小说,因为它们被时间空距离分隔开,表面上指向童年记忆,但实际上指向成人世界的喜怒哀乐和社会苦难,因而也具有思考和审视的功能。
与《城南旧事》相比,《呼兰河故事》的复调叙事更加突出。《呼兰河传》由七章组成,没有固定的人物。前两章主要描述呼兰人平凡琐碎的生活和当地的条件与习俗。他们是从成年人的角度来描述的。接下来的四章主要从儿童的角度进行叙述,但正是这些章节中隐含的成人视角和儿童视角的反复出现使得作品的复调意义更加明显。
任何写作只能是一种当下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呼兰河传》是萧红对当下存在的心理支持的探索。作者的情感总是穿梭在过去和现在两种时态空之间,这在潜在的两种生存系统之间形成了相互对比,使读者觉得作者的记忆总是徘徊在温暖童年的记忆和现实之间。”一旦叙述者沉浸在他童年时对祖父和后花园的回忆中,叙述的语气逐渐升温。然而,当记忆结束时,真实的情况会利用它们,悲伤的情绪会很浓,这将最终形成整部小说的贯穿主题。童年记忆不仅成为过去,还通过记忆延续到现在,这种延续融合了作者对人类生活、人性等问题的思考,直接指向生命的本质意义,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
呼兰河传第四章写的是我的庭院,每句话都以“我的房子很荒凉”和“我的庭院很荒凉”开头。从孩子们的角度来看,它描述了工厂车间、粉末车间的故事以及祖父教给我的认可。当写这些故事时,它总是以成人的形式不经意地得出结论。我一说完,闪闪发光的白色粉末就像瀑布一样,然后我就“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活很遗憾,但我不在乎。你看起来很危险,但我认为我为自己感到骄傲。不骄傲怎么样?生活比快乐更苦”[7。这是萧红对呼兰市麻木无知的反思,也是她对生活的反思和审视。
小团圆的儿媳妇在我眼里只是一个黑皮肤长辫子的小女孩。在成年人眼里,她被认为是被邪恶所附体,因为她慷慨大方,谦逊有礼。对于那些“关心”小团圆媳妇病情的旁观者来说,“积极”贡献想法和旁观者的生动场面,“我”一直是旁观者,如实描述,不加评论。直到她成年,小红再也无法忍受了。小团圆的婆婆给她写了一篇长篇演讲:“当她来到我家时,我没有给她任何愤怒。一家人都不生气的重聚媳妇,她一天被打八次...有几次,我把她挂在大梁上...我还用炽热的熨斗烫了她的脚背……”
小时候,“我”记不起小团圆的妻子和婆婆的长篇大论。成年萧红的视角和话语表达逐渐泄露出来。小团圆的媳妇和婆婆的无知扮演了一个杀人犯的角色,毁了一个健康、活泼、年轻女人的生活。在无知的呼兰市,这很常见。人类的生活甚至比植物和动物还要糟糕。这是多么荒谬和悲惨啊!萧红对愚蠢的传统道德杀戮的反抗是激烈的、愤怒的和不可容忍的。《城南旧事》由五个完整的故事组成,每个故事都有英国儿童参与,从而确保了相对完整的叙事视角。复调音乐没有呼兰河传说那么明显。
利用聪明、聪明、善良的英子,她参加了社会底层的疯女人秀珍、妞妞、偷、兰阿姨和马松的生活。英子不知道谁“好”,谁“坏”。她只知道秀珍被她的爱人抛弃了,她的孩子也被抛弃了。她被别人视为“疯子”,因为她无法忍受情感的打击。我只知道这个可爱美丽的女孩仍然每天被养父养母殴打。当《疯女人》秀珍和她精心讲述她与司康和瑛子的美好关系时,小英可能不理解秀珍的感受,但读者清楚地读到了成年的林海印对秀珍的无限同情和辛酸。当小偷告诉英子失明的母亲、她杰出的兄弟和她贫穷的家庭时,英子可能不明白为什么小偷会告诉她这些,但是成年的林海印清楚地知道小偷在表达他的痛苦和遗憾,并且理解小偷的行为。
城南的故事通过英子看似温暖、慈爱和幸福的生活,揭示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英子看似理解他们的生活,实际上对整个旧社会的人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然而,林海印对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给予了更多的同情。至于为什么以及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她似乎还没有考虑过。对于传统习俗和道德,她更认同和回归。
虽然《城南旧事》总体上温和、真诚、色彩鲜明,但在多次离别后,作品仍充满悲伤。在《城南旧事》中,出现在毕业典礼上的李戈和上一代毕业生的离去,是成年的林海印对频繁分离、易腐欢乐和短暂人生的哀叹。肖英姿不明白他周围的人为什么总是悄悄地离开,但无论是成年的林海印还是读者都很长时间没有想到“成长”和“离别”。
三个孩子的性别意识
孩子们了解世界的方式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的认知风格与她们的相似。这为成年女性作家从女性和儿童的角度进行创作提供了便利。一方面,他们表达了童心,童心,与孩子有关的纯真;另一方面,它们结合了女性的美丽、精致、优雅和深度。小红和林海印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他们非常关心妇女的命运,对旧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呼兰河传》和《南城旧事》中的“我”和“瑛子”都是小女孩。他们的性别非常重要。这个女孩缺乏经验、天真和对女性的自然态度使得用眼睛看成年女性的生活变得很自然。如果“我”不是一个小女孩,“我”就不会和小团圆的儿媳妇说很多次话,也不会对王小姐和她的孩子们如此好奇。如果英子不是小女孩,她就不会和那个女孩成为好朋友。她总能找到秀珍一起玩。“我”和“英子”都是作者、叙述者和主角。这三者的结合表明,女性的叙事倾向于采用故事化的叙事策略,突出女性的“声音”,[9]。
(一)女孩的悲剧观
《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涉及许多女性形象。从孩子的角度来看,这些女人大多是执着、善良、聪明和诚实的,但最终的结果不是很好。《呼兰河传》中小团圆的儿媳妇和王小姐是一个皮肤黝黑、辫子长长的小女孩,一个声音洪亮的大女孩,一张幸运的脸,每个人都称赞她。但是最后一个被她丈夫的家人虐待,被热水烫伤致死。一个人在被别人嘲笑和愚弄后死于分娩。《城南旧事》主要描写疯狂的秀珍、可怜的女孩、失去孩子的马松等。
《呼兰河传》中的王小姐和《城南旧事》中的秀贞有着相似的爱情悲剧。在公众的嘲笑和谩骂中,王小姐坚持要和冯伟嘴呆在一起。以前所有人称赞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男人想长胖,女人想长嫩。我没见过像个大女孩的女孩。秀珍爱上了穷学生司康,怀上了她的孩子,但司康再也没有回到她的家乡。这个新生儿被父母遗弃了。秀珍受不了精神上的冲击,终于崩溃了。他们的爱情以悲剧告终,但他们都有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和决心。秀珍和司康的对话:“我妈妈独自生下我,和你一起去吃红薯。她怎么能放弃我?他说,你是个孝顺的女儿,我也是个孝顺的儿子。如果我妈妈抓到我并禁止我再来北京怎么办?我说,那我就追你。[道:“秀珍终不能出京,王小姐也不能出坊。”。他们的爱是与传统力量的斗争,但他们太软弱,注定以悲剧告终。
《呼兰河传》中小团圆的媳妇和《南城旧事》中的女孩命运相似:她们都是弃儿。小团圆的媳妇是胡夫一家买的媳妇。在胡夫家族和呼兰市的人们看来,所有对她的殴打和责骂都是理所当然的。她甚至不如鸡鸭。打鸡鸭也面临经济损失的风险。只要她不被打死,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小团圆的儿媳妇仍然被他们烫伤致死。她的婆婆为这5000元感到苦恼。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没有太多的乐趣可看。没有人同情她。呼兰市的人们,就像那里寒冷的冬天,敲碎了大地和小红的心。如果不是从一个女孩的角度来描述,请上帝洗澡只是一种习俗的再现,不会显得那么令人兴奋。女孩的视角使得洗澡的肇事者和整个过程成为读者观看的中心。小团圆的儿媳妇和她丈夫的家庭的心理似乎被投射到一个巨大的屏幕上,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萧红用描述呼兰人看热闹的话语对无情、麻木、残忍的呼兰人进行了无声的指责和指责。这个女孩出生时被祖父抛弃,养父母经常殴打她。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亲,但在去找父亲的路上被火车辗过。除了和英子的温暖友谊,她似乎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体验痛苦。中年的林海印再次回忆起他童年时的朋友,但这难道不是怜悯和悲伤吗?
(二)女性对女性的误解
《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在人物设计和叙事策略上具有明显的性别意识。叙述者“我”和“英子”都是小女孩,代表着一种不受任何世俗事物污染的生活和视角。呼兰市的妇女、英子的母亲和宋的母亲是传统道德和文化的代表。在《呼兰河传》和《南城旧事》中,这些悲剧女性被女性误解了。
在《呼兰河传》中,王小姐不顾公众的嘲笑,与冯伟嘴结合在一起。店主的妻子在磨坊里大声责骂,称王小姐为不洁的野妻子。她大喊大叫,冻死了,同时她取下了唯一一个温暖的脸袋,残忍地盖住了王小姐和孩子们,不管他们的死活。杨太太、奶奶和所有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面粉厂的人都没有说王小姐不好。在他们眼里,王小姐是可耻的,坏的,不值得同情。在萧红眼里,这些被传统思想禁锢的女人是悲伤、麻木和愚蠢的。萧红平静的叙述背后,有一个对呼兰女性的讽刺。如果女人不了解女人,她们怎么能反对父权制的权威呢?《呼兰河传》第二章讲述了4月18日娘庙会的民俗:“先去老爷庙,敲钟,敲你的头...然后去娘庙”。“皇后一定害怕被主人打...可以看出,男人殴打女人是很自然的,神和鬼是一样的。难怪娘娘庙里的皇后如此温柔,经常挨打。”[14]
一方面,萧红表达了她对女性的悲伤和同情,另一方面,她极度讽刺父权制的邪恶。萧红更加关注人们的精神麻木和冷漠,以及传统道德文化对人们的禁锢和毒害。她指出了这一点,并质疑妇女的生命尊严。
与萧红激烈的抱怨、挣扎和失望相比,林海印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传统女性,更多的是同情、默许和无助。《城南旧事》中的马松是英子一家的保姆和奶妈。为了这个贫穷的家庭,马松一生下孩子就去了城里工作。她很好地照顾了英子兄妹的生活,但是她有四年没有回家了。她的儿子已经去世两年了,她的女儿被送走了。她甚至不知道!她把辛苦挣来的钱都给了丈夫,丈夫把钱“给”了赌场。然而,在文章中,马松没有批评或质疑她的丈夫,除了默默哭泣和试图找到她的女儿。当英子的母亲催促马松时,她说:“小栓子和女仆应该被排除在你的生活之外。我能做什么?”
从英子的母亲所说的,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女性一刀切的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女人不了解女人,也不了解自己悲剧的原因。他们并不认为丈夫的不负责任导致了孩子的悲惨命运,而是命运捉弄了人们!林·海印的叙述一直很平静,没有愤怒、讽刺或反抗。她对男人和社会的批评是温和的。林海印从小的生活和她嫁入一个传统大家庭的经历使她基于自己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识而对女性产生了关注。她有时甚至扮演这些传统的女性角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她对传统儒学的认可和回归。
综上所述,《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既有儿童视角下的欢乐、纯真和多彩色彩,也有隐藏在儿童视角下的成人视角下的悲伤、失望和无助。然而,同样是强烈的乡愁和记忆美学呈现给读者。萧红和林海印在他们的作品中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奋斗。他们对家乡的强烈渴望使他们有着相似的情感和相似的表达视角,但他们不同的生活经历使他们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直面虚无,消除孤独;看看自己的祖国,寻找文化的根源。无论萧红坚持宁死不屈,还是林海印从幸福的家庭中退缩,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对女性命运的关心,对人性更美好的热切希望,对家乡的回眸,对社会的审视,以及对最纯洁孩子眼中生活的质疑。
参考:
【[1】熊嘉良。中国近代小城镇文化与小城镇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107。
[2]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81。
[3]林·海印。《[城南的古老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
[4]小红。[永恒的渴望和追求∑萧红。萧红全集:第二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1044。
[5]吴晓东、倪文健、罗刚。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1999 (5): 67-75。
[6]吴晓东、倪文健、罗刚。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书,1999 (5): 67-75。
[7]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84。
[8]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07-108。
[9]程国军。从乡愁到性别斗争[·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0。
[10]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68。
[11]林·海印。《[城南的古老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1。
[12]艾晓明。20世纪文学与中国女性[。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3-14。
[13]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49。
[14]小红。呼兰河传记,小镇行军[。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50。
[15]林·海印。《[城南的古老故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