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美学根源,中西悲剧的异同
探寻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美学根源
中西悲剧的异同中西悲剧的异同在于:1 .不同点:中国悲剧是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悲剧,而西方戏剧是以命运本身为中心的悲剧。钱学森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元》没有油去挖掘窦端云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和他救婆婆生命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这种内部悲剧冲突,却描述了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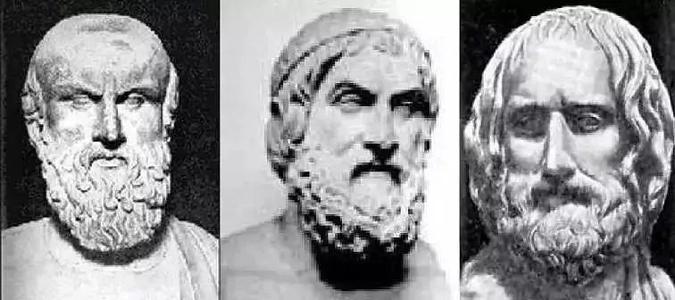
西方悲剧发展的阶段及概况
西方悲剧已经从古希腊悲剧发展了2500多年。 随着悲剧的辉煌发展,许多著名的悲剧理论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莱辛、席勒、黑格尔等出现了。 他们的悲剧理论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并不断成熟和完善。 西方悲剧应该从希腊开始,希腊展现了汉字的“为他人而生”和西方人物的英雄情节。西方惩罚自己。窦娥是封建社会下层的小人物,两者都被摧毁了。哈姆雷特以死亡和毁灭的极端构建了崇高而悲剧的悲剧意识。 第四,窦张甜将导致悲剧的结束,人物将战斗到底。 哈姆雷特,1岁。不同选材(1)题材来源:中国古典悲剧大多描写社会现实。关汉卿生活在元代社会的底层。通过窦娥元,他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压迫、愚昧和无能,赞扬了窦娥的战斗勇气 西方悲剧大多基于神话、传说和史诗。哈姆雷特是根据丹麦传说改编的。与此相一致,中国古代的四大喜剧是关汉卿的拜月亭、王实甫的西厢记、白璞的《关马墙》和郑光祖的《钱女李勋》。 四大悲剧分别是《窦娥原》、《韩公秋》、《吴桐宇》和《史昭孤儿》。西方著名的悲剧有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Xi。中国古代喜剧与西方喜剧精神的异同:(1)西方喜剧一般只用于讽刺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章指出:“喜剧总是模仿比今天更糟糕的人。” 古希腊匿名的《喜剧大纲》说:“喜剧是针对一种荒谬的、有缺陷的、有相当长时间模仿的动作 “这部传统喜剧,
中西悲剧的异同
中西悲剧的异同中西悲剧的异同在于:1 .不同点:中国悲剧是以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悲剧,而西方戏剧是以命运本身为中心的悲剧。钱学森认为关汉卿的《窦娥元》没有油去挖掘窦端云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和他救婆婆生命的愿望之间的矛盾。这种内部悲剧冲突,却描述了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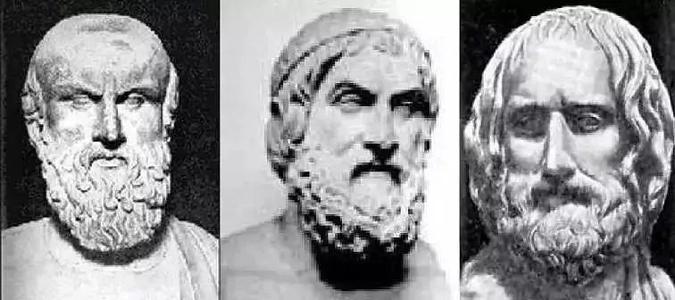
西方悲剧发展的阶段及概况
探寻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艺术表现方式及美学根源范文
摘要:受儒、道、佛的影响,中国悲剧艺术呈现出不同于西方悲剧的形态特征,如道德伦理的教育功能、类型化人物的设置、悲喜情节的设置、幸福结局、超越精神与和谐等。然而,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这些作品的悲剧本质。无论是《赵氏孤儿》、《窦娥元》、《桃花扇》还是《红楼梦》,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悲剧氛围和悲剧观念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探究中国悲剧艺术的审美基础,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对悲剧观念的独特理解,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儒道思想;中国悲剧;教育职能;超越精神;和谐的特征;
自王国维1904年发表《红楼梦评论》和1913年发表《宋元戏曲考》以来,悲剧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悲剧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并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所以中国文化中是否存在真正的悲剧理论和作品在学术界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从辛亥革命前后是否有悲剧的争论到建国后的比较文学研究,对中国悲剧、悲剧意识和悲剧作品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但没有达成共识。有两个主要障碍。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亚里士多德的“诗歌艺术”这样的悲剧专业化,也没有专业化的理论体系。其次,中国悲剧作品如《窦娥原》、《桃花扇》、《赵氏孤儿》和《朱良》往往表现出不同于西方悲剧的特点,如主人公在道德伦理约束下人格的萎缩、悲喜交替的结构特征以及“幸福”结局等。这些特点使得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作品与西方悲剧理论相矛盾,甚至相矛盾。基于以上两点,本文试图从儒、道、释三方面探讨中国文化对悲剧的独特理解,探索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不同于西方悲剧的艺术表现和审美根源,并试图回答中国是否存在悲剧等长期争论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悲剧的教育功能
儒家学派是第一个对中国传统悲剧艺术产生重要影响的学派,因为自先秦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西周的礼乐制度。因此,学校高度重视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和伦理属性。例如,《礼乐全书》认为“喜欢音乐的人也喜欢圣人的幸福,可以善待人们的心灵。”它感人的深度,它的风格和习俗的变化,所以第一个国王教它如何“[1]539”,快乐地没有抱怨,礼貌地没有争议。对于那些臣服于王位并统治世界的人来说,礼仪和音乐也被称为“[1”531。虽然这不是直接谈论悲剧艺术,但礼仪和音乐教育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已经成为中国悲剧艺术创作和评价的重要标准,例如悲剧《剑的故事》的作者李开贤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意义高、音调古、音调和谐, 并且能够唤起和说服人们的感情去感动”和“鼓舞和说服人们的心,感受和远离正派,不仅仅是做事,不赚钱,不赚钱”[2]52。 这完全符合儒家用礼乐教化民众的宗旨。陈洪寿在《元阳义墓焦红故事》的序言中还说,“一个演员演一只狗,喜欢叹息和哀叹,这使人的性情发生了变化。所有好人都会说服他,而所有坏人都会生气。这是对一百名道学家的训练,不像演员的力量。“[2]224这是一种观点,认为好的作品可以通过触动人们的心灵来微妙地影响人们的气质,从而达到化恶为善的效果。卓任玥直接肯定了悲剧艺术在教育人和改变风俗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新西厢记》的序言中说:“丈夫的戏剧是以风的世界为基础的。风如此之大,以至于人们从悲伤和快乐中解脱出来,对生与死漠不关心。生活和幸福,这一天鸩人也的原因;悲伤和死亡,天堂之所以是玉也。首先,正如世界所做的,当一个人悲伤时,他仍然不会忘记快乐;当一个人被处死时,他仍然不会忘记生命;当一个人悲伤和死亡时,他还不足以成为一个人,风是什么?”[2]298这是一种观点,认为纯粹的喜剧只是麻痹人的毒药,只有真正的悲剧才能使人超越痛苦,对生死无动于衷。由此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感动观众,产生“感动道德”、“鼓舞人心”的效果,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悲剧艺术最基本的创作动机和评价标准,但这种创作动机和评价标准直接影响着传统悲剧艺术的主题、情感表达和人物形象设置
从创作主题来看,儒家的忠孝仁义礼智价值观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悲剧艺术教育的道德标准和表现对象。例如,《赵氏孤儿》中300多名赵盾家庭成员被屠杀的悲剧,就是由屠岸贾陷害忠良所代表的奸臣造成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傕、公孙朱、程英等人在《寻找孤儿》和《拯救孤儿》中的忠诚。该剧通过比较展示了儒家的“忠”和“义”的概念。在《琵琶记》中,面对灾难,赵武娘尽最大努力向叔叔阿姨表示敬意。他宠坏自己并希望举行葬礼的行为令人感动。这是为了弘扬儒家的“孝”和“仁”的价值观。在《窦娥元》中,窦娥的贞操和孝道代表善的力量,而张吕尔等人则代表恶。这也通过比较凸显了儒家的“孝”和“礼”(特别是女性的贞操)价值观。“朱砂熊”深刻批判了王文勇因缺乏对话信仰而导致的悲剧行为,强调了儒家“信仰”和“义”的社会价值...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中的大部分主题都隐含在儒家价值观中。
从情感表达机制来看,儒家的“中和”和“适度”原则也影响了中国传统悲剧的表达机制。儒家认为,人性的本质状态不是“喜怒哀乐”中的任何一种情感,而是“喜怒哀乐”之前的平静状态尚未显现出来,也就是说,“中庸”说:“喜怒哀乐的缺失是指中庸;这是两者的总和。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首都。而且,道的世界也是如此。为了达到和谐,天堂没有位置,万物都是被滋养的。”[3]289根据这个标准,悲剧艺术的“启蒙”目的不是让观众达到一定的情感高潮(就像西方悲剧中的“崇高”和“震撼”效果),而是让观众在经历了一些痛苦的经历后,能够分清是非、善恶,回归理性的平和与安宁。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悲剧中,如果剧中人物的命运太悲惨或灾难太强烈,那么在故事的结尾,往往会做出某种程度的情感补偿,以安抚观众的情绪。例如,《赵氏孤儿》的结局就是赵氏孤儿长大了。程英说了实话,并在姜维部长的帮助下攻击了他的敌人。巨大的敌意得到了回报,正义最终得到了伸张。另一个例子是窦娥元的终结。窦娥的父亲窦张甜回来当了一名官员。窦娥不公正的灵魂似乎诉说了他的不满。窦张甜惩罚了恶人,窦娥的不公得到了纠正。这种结构安排是后来中国悲剧研究中经常提到的“团圆”结局。它的建立也是为了使作品达到一定的启蒙效果(即“中和”)。
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悲剧通常是以“脸谱”(facebook)和类型学的形式来设置的,即悲剧作品中的大多数人物都有非常鲜明的性格特征,要么善良要么邪恶,要么忠诚要么奸诈,观众甚至不需要情节就可以通过“脸谱”粗略判断。这种“脸谱”和类型艺术手法与儒家严格区分君子和小人、义利有着相同的效果,服务于“音乐教学”和“道德”的理念。李渔在《休闲偶发性发帖·词曲部》中说:“如果你想说服人们孝顺,你应该给孝顺的儿子取个名字,但如果你有纪律,你就不必事事都做。如果任何一个孝顺的家庭成员都应该把它拿走并归还,这对周来说还是不够好。最好认真对待它。如果一个人生活在低处,世界上所有的邪恶都会回来。“[4]24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悲剧艺术在刻画人物时并没有涵盖所有方面,而是经常运用人物性格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一点来进行艺术表达。例如,《赵氏孤儿》中的屠岸贾把赵氏家族的300条生命视为粪土。他甚至牺牲了全国各地婴儿的生命来杀害孤儿,这可以说已经达到了非人化的程度。另一个例子是《琵琶记》,其中赵武娘为了纪念缺衣少食的叔叔婶婶,宁愿“自己吞糠”。当我叔叔和婶婶去世时,他们无法把尸体送到葬礼上。他们愿意出售他们的头发,这样他们就可以有棺材来运送他们的尸体。当她的岳父写了一份遗嘱允许赵武娘在死前再婚时,她拒绝服从等等。结合许多行为,可以说赵武娘不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典范,体现了古代女性所有美丽的道德品质。
中国传统悲剧中的“脸谱”和典型人物塑造明显不同于西方悲剧。程朝祥在《悲剧中的人——中西悲剧英雄之比较》中详细分析了这种差异:“中国悲剧英雄倾向于认同类型”、“他们的人格倾向于萎缩”;“西方悲剧英雄倾向于将个人区分开来,“个性”倾向于扩展“[5”。谢百亮在《中国悲剧纲要》中说:“只要我们密切关注我国的古典悲剧,不难发现他们的性格不够主观,意识不强,一切都处于悲叹的被动状态。这是中国悲剧的通病。”[6]312~313张敞也在《中国悲剧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中质疑:“这些是中国悲剧英雄吗(如窦娥、岳飞、汉元帝等)。)谁被命运发现在头上,谁的人格在邪恶势力面前一步一步退缩,最终被摧毁成“悲剧英雄”?还是降低要求是一个悲惨的数字?”[7]这种怀疑不无道理,因为从西方悲剧理论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悲剧中的许多人物都不符合真正的悲剧精神。在西方文化中,一个真正的悲剧人物必须具有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和高尚的人格。“如果苦难降临在一个性格软弱的人身上,他无可奈何地接受苦难,那么这就不是真正的悲剧。”[8]206。这也是许多学者怀疑悲剧艺术是否真的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作者认为,中西悲剧类型性格设置的差异是由两种悲剧创作主题和接受者的不同以及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学艺术体系造成的。中国传统悲剧大多以歌剧和小说的形式出现。它的主要目标受众是底层的普通大众。其目的是道德教育和文化传承。然而,西方悲剧属于精英文化。例如,古希腊悲剧主要是针对城邦贵族的。显然,“脸谱”和典型化的人物设置方法更有利于普通人的接受,也更容易清晰地表达作品所包含的道德价值和文化内涵。这正是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与避讽刺》中所说的,“因为很少有人能读书识字,愚蠢的丈夫和愚蠢的妻子被劝告要善良,戒律不是邪恶的,他们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因此,这样的话是借用上层人士的话说“[4]9。然而,西方悲剧的艺术表现方法显然不能很好地满足这种现实需要。此外,中国传统悲剧分离和美化人物的方式本质上属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写意”体系,就像中国传统绘画一样,它只捕捉绘画对象的最具特色的特征并加以展示,而忽略了其他细节(从西方悲剧理论的角度来看,它成为“人格萎缩”);西方悲剧创作中的人物都是个性化的,如俄狄浦斯、奥赛罗、哈姆雷特和茶花女。他们的性格全面全面,非常接近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复杂性格,这实质上是西方的一种“现实主义”传统。两者的区别就像中国文人画和西方油画的区别一样。显然,我们不能用中国绘画的“生动描绘”标准来评价西方油画。同样,我们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悲剧标准来要求和评价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事实上,“写实”和“写意”都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悲剧作品。虽然《赵氏孤儿》、《窦娥元》等许多中国传统悲剧作品不符合西方悲剧精神和评价标准,但我们不能说它们不是悲剧,它们生长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表现出不同的艺术形式。
2。道教与中国悲剧的先验精神
道家学说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但道家思想对悲剧艺术的影响并没有偏离儒家思想设定的基本坐标,如上述育人功能、典型的“写意”手法、回归人性的目的等。然而,道教在教育人和理解人性方面与儒家不同,从而为中国传统悲剧艺术的创作增添了新的元素。道教认为儒家的仁义礼智价值观并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反而会引起人们心中的困惑。比如《老子》说:“不上仙,使人不争;不贵的稀有商品,使人不偷;没有欲望,让人心不乱“[9]6号”,绝生启智,人受益百倍;弃仁弃义,还民以孝;没有聪明的放弃利润,盗贼就没有“[9]45。这些是对儒家价值观的直接否定。庄子对儒学的批判更为精辟:“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知识分子不为贼积累?所谓的圣者,有没有人不提防小偷?......因此,绝对的圣人放弃知识,大盗被制止,玉毁珍珠,小盗负担不起。”[10]149~150这实际上是儒家圣人和智者作为“大盗”危害国家,而仁义礼教和智慧的价值是窃取国家的工具。
道教批评儒学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儒家价值观是相对的,不能被视为绝对正确的标准。老子说:“世界知道美就是美,邪恶已经发生了。众所周知,好是好,但不好。因此,不管有没有相互生成,难度和难度是相辅相成的,长度和长度是比较的,程度和程度是倾斜的,声音和声音是结合的,前后跟随。”[9]4也就是说,善、恶、美、丑的价值观都是相对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外部条件可能导致它们向相反的方向转变。第二,儒家价值观违背人性的本质。他们不会教育人们,反而会适得其反。庄子说:“正确对待钩和绳的人就是切断性别的人。那些等待绳子被漆捆住的人就是那些侵犯他们道德的人。弯曲仪式和音乐,或理解正义和正义安慰世界的心,将失去他的常然。”[10]136这实际上是儒家的价值标准作为约束人们规则的绳索,会使人们失去他们的自然本性。鉴于以上两点,道家提出了超越相对性和世俗性的价值标准:“礼即世俗性”真的,所以到了白天也一样,自然不容易。因此,圣人的法律是高尚的和真实的,他不坚持世俗。”[10]539下面结合传统悲剧作品具体说明了道教的影响。
从作品的主题来看,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一些传统的悲剧作品也涉及到对儒家价值观的反思和批判。例如,《琵琶记》中的蔡伯杰就面临着忠义孝之间的困惑。他熟悉儒家经典,严格按照儒家道德标准工作,但总是面临各种无奈的矛盾。他无意成名,只想跪下孝敬父母。然而,他的父亲蔡红跟随读《光宗耀祖》的想法,不顾实际情况,开车送儿子去北京参加考试。父亲的生活难以违抗,导致与新婚妻子赵武娘分居,赵武娘不得不独自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蔡伯杰在考试中获得一等奖后,想辞职回家为父母服务。然而,他无法抗拒皇帝的圣旨,即“孝是如此之大,他最终为国王服务,国王很难为他的父亲服务。”尽管蔡伯凯总是按照儒家的价值观行事,但他会陷入尴尬的境地,要么对国王“不忠”,要么对父亲“不孝”,要么对妻子“不公正”。另一个例子是“朱姬发”,面对战争带来的灾难,徐小可再也不能承担赡养妻子和母亲的责任。一个是同甘共苦的妻子,另一个是生下自己的母亲。他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最后,他卖掉妻子去救他的母亲。尽管他很“孝顺”,但他对妻子“无情”、“不公正”。上述悲剧作品都涉及到对儒家价值观相对性和局限性的反思,这在原则上与道家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一致的。
从表达机制来看,道教反对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对人心的限制,主张“法律和自然重视真理”的原则。因此,儒家的“和”原则,即“乐、怒、悲、乐不可言,以和为贵”也在一定意义上得到了突破。例如,《淮南子·颜泉训》说:“如果你要唱歌,你不会感到悲伤。如果你必须成为一名舞蹈演员,你就不能为自己骄傲。那些唱歌跳舞而不是悲伤和美丽的人没有根。”[11]1025~1026,也就是说,艺术情感表达的关键不在于“中庸”,而在于现实。只有有真实感情的艺术才能真正打动观众的心。这是对儒家“中和”原则的突破,因为真正的情感比“中庸”更接近自然人性,圣人也不例外。例如,戏剧《牡丹亭》中就有这样一个细节。当这位老学究把“关雎”解释为“皇后和智者”以及“宜家在适当的房间里”时,英雄杜丽娘敏锐地意识到:“圣徒的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和过去一样,不是吗?”[12]2093难道不是剧作家汤显祖自己的艺术思想在这里表达出来的吗?杜丽娘的“真实感受”和“极端感受”不仅是对某个异性的依恋,而且是基于一个人的自然欲望和情感以及生活中最基本的需求。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在现实生活中没有遭遇任何阻碍或挫折,而是死于一场梦。这似乎不是悲剧,但她的真正死因是儒家思想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对自然人性的扭曲和压制。这无形的网使她无法挣扎、逃脱,甚至抱怨,最后窒息而死。汤显祖通过杜丽娘之死批判了儒家“中庸”思想对情感的局限,展示了“真情”和“至善”的价值。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说:“全世界的女人都像杜丽娘一样善良。梦见的人是疾病,疾病是“平的”,以手绘的描述传递给世界然后死去。三年后,恢复梦想的人出生了。比如李娘,就是情人的耳朵。我不知道我在做什么,但是一旦我死了,活着的人可以死,死去的人可以住在一起。生命不能与死亡联系在一起,死亡也不能与复活联系在一起。爱情也不能。”[12]1153《牡丹亭》追求“真情”、“极端感情”的表达机制,是道家“法、天、道”的生动体现。除了《牡丹亭》之外,《梁祝》、《焦红记》、《柴吉川》等悲剧作品在表现机制上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
从作品的结构特征来看,道家思想也对传统悲剧的戏剧结构和情节设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前所述,老子的“是否存在,困难与困难相辅相成”的思想,“悲伤”与“幸福”也是相互依存的范畴。俗话说,幸福招致悲伤,幸福不会结束。中国传统悲剧作品往往通过情节设置中“悲”与“喜”的相互对比和转化来表达主旨。例如,在《琵琶记》中,创作者安排了两条线索。一个是蔡伯杰进入北京参加考试。另一个是赵武娘对老人的服务。赵武娘与蔡伯杰奢华生活的悲剧经历形成了“悲伤”与“幸福”的鲜明对比:蔡伯杰正在饮酒赏月,赵武娘吞下了谷壳。赵武娘哀叹化妆时,蔡伯杰正在杏园享受春天...悲伤和快乐的对比凸显了戏剧性的冲突,增强了悲剧气氛。另一个例子是《牡丹亭》,其中杜丽娘的生活单调沉闷,令人“难过”;在女仆春香的陪伴下,她欣赏五彩缤纷的爱情,从“悲伤”中诞生“快乐”。然后她突然意识到她的青春就像春天的风景,充满了色彩,但是没有人欣赏。她最终会“把它交给这口破井和废墟”,并再次“快乐”和“悲伤”。在梦里,她遇见了她的爱人刘梦梅,此时她从“悲伤”中“快乐”。然而,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再次让她陷入绝望,最终死于她的梦想...从以上两个案例中不难看出,道家思想影响下的传统悲剧在情节和结构安排上充满了辩证性。既没有绝对的“幸福”,也没有绝对的“悲伤”。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相互对立,甚至相互转化。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文学艺术中“喜剧”与“悲剧”的二分法,所以从西方悲剧理论的角度理解为什么中国传统悲剧作品基本上不是典型的、严格的“悲剧”。
此外,道家思想为传统悲剧作品的圆满结局注入了新的内涵。儒家影响下的“团圆”结局主要停留在世俗层面和道德层面,而道家影响下的“团圆”结局往往超越世俗,超越世俗道德观念和世俗标准。例如,《梁祝》中的“变成蝴蝶”,以及《牡丹亭》中杜丽娘因梦而死和复活的最后情节都不符合现实生活经验,而是超越了现实生活。它们就像老子描述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和陶渊明描述的“乐园”。它们是浪漫的想象,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美丽梦想,体现了道家的艺术理想,超然于世俗,追求最大的爱与自然,“法律与天堂是珍贵而真实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思想使中国传统悲剧艺术具有超越世俗世界的性质。
3。佛教与中国悲剧的和谐
如果儒家赋予传统悲剧艺术入世的启蒙功能,道家赋予传统悲剧艺术出世的超然精神,那么佛教理论赋予它入世与出世的双重属性,使二者有机地融合在悲剧艺术中,这是因为与儒家价值观的局限和道家审美理想与现实的脱节相比, 佛教为传统悲剧艺术提供了更完善的理论体系和客观价值标准,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是“因果”理论,出生与入世之间的矛盾统一在“因果”的客观规律中。 所谓“因果”是“因果”和“报应”的简称。口译员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因原因和条件而产生,即“因果报应”。其中,“原因”是指事物的内部原因,“命运”是指一切外部条件。当“原因”和“命运”都存在时,就会产生某种东西,这就是“因果报应”。“因果报应”理论与现代科学精神是相通的,因为科学研究也是基于因果关系的规律,所以解释者的“因果关系”概念与儒道相比不是主观的,更接近于客观规律。然而,与现代科学不同,佛教的“因果”普遍适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事物,不仅包括物质现象,还包括精神现象、生活活动和社会生活。受此影响,在中国传统悲剧中,创作者往往会规划布局、安排情节发展,甚至从“因果”的角度思考悲剧的成因和解决方案。
该剧以孔任尚的《桃花扇》为例,以李项峻和侯方域的爱情故事为中心,高度集中了明代崇祯末至南明弘光政权倒台期间发生的各种历史悲剧。其中,不难发现作者对明朝灭亡的“报应”的思考:南明皇帝和官员的腐朽统治;长江以北的四个城镇自尊自爱,互相残杀。左良玉不顾大局,率领大军向东进发。史可法虽然忠于学习,但缺乏权威,他只能独自战斗,为国家而死。在上述“因果报应”的相互作用下,明朝的灭亡似乎成了历史的必然。无论史可法、刘敬亭、李项峻、侯方域等人如何努力,他们都无法改变这场历史悲剧的表现。最后,史可法跳进河里自杀,刘敬亭成了渔夫,李项峻和侯方域都成了和尚和尼姑。可以说,《桃花扇》从一个非常广阔的社会历史视角来看待因果报应的普遍性、客观性和不可逆性。
口译员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悲剧都是通过种植“苦果”而获得的“苦果”,这些苦果在成熟时是无法改变的。因此,从现在起,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堵住“恶因”,避免“苦因”的成熟,并在此基础上积极培植“善因”,培育“善因”,使“善果”尽快成熟。即使是出生后的解放,也需要首先播种“好的事业”,培育“好的事业”,才能获得最终的“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在世界上引起痛苦的“业力”被称为“积德”(烦恼的聚集),痛苦的“果实”被称为“苦娣”(世间生活的本质),出生的“业力”被称为“道娣”(解脱的道路),出生的“好果实”被称为“灭娣”(烦恼的消除)。因此,佛教的\"苦\"、\"吉\"、\"灭\"和\"道\"的核心教义实际上是在因果法则的基础上统一的。因此,“因果法则”已经成为统一生与入、悲剧与解放的关键点。除了前面提到的《桃花扇》,按照佛教因果理论编排的悲剧作品还包括王国维称赞为悲剧的《红楼梦》。
以《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例,如果他们的爱情悲剧被视为“报应”,那么这种报应的前因就是深红珍珠仙子和申英侍者之间以前的爱情关系,也就是说,深红珍珠仙子能够被申英侍者的雨露塑造成一个人,为了报答恩情,她与申英侍者一起下凡创造了一种神奇的关系。曹雪芹透过绯红珍珠仙女的嘴说,“他是甘露,我没有这样的水可回。他为世界服务,我也为世界服务,但我可以用我一生的眼泪来报答他。”[13]8因此,林黛玉总是在《红楼梦》后的几章中为贾宝玉哭泣,直到她泪流满面。前后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多不少。另一个例子是王熙凤,他说他“从来不相信地狱的报应是什么”。我说过我会做你想做的任何事”[13]213。然而,作者仍然没有让她跳出因果循环。也就是说,“器官太聪明”是“因为”,而“你生命中的错误”是“果实”。甚至王熙凤唯一做的好事——帮助刘姥姥——也终于得到了相应的“好结果”,那就是她的女儿巧姐终于被刘姥姥救了。如果仔细分析,《红楼梦》中“草蛇灰线绵延数千里”的写作手法贯穿着各种复杂、互动、纠缠的因果链。
《红楼梦》在因果规律的基础上也有价值,因为它通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揭示了人生痛苦的本质和原因(痛苦的真理和集体的真理),并通过贾宝玉等人的经历思考了缓解痛苦的目标和方法(灭绝的真理和道德的真理)。王国维曾将《红楼梦》评价为“一部完整的悲剧”,关键在于此。例如,对于所有悲剧的根源(即时嘉的《史记》1),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
生活的本质是什么?这只是愿望。对性的渴望是贪得无厌的,但它源于不充分。不足的状态,痛苦也是。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满足,那么这个愿望就会结束。然而,想得到补偿的人是想得到补偿的人,不想得到补偿的人是想得到补偿的人。他想追随一个结束的愿望。因此,安慰是不存在的。即使我们想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与此无关,我们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疲劳。......可以去掉这两个,我们称之为幸福。然而,当我们寻求幸福时,除了内在的痛苦,我们还必须努力,而努力也是痛苦之一。快乐过后,痛苦也更深。......这种痛苦随着世界文化而增加,而不是来自文化。什么事?文化进步越多,它拥有的知识越多,它想要的就越多,感受到的痛苦也就越多。然而,生活的欲望不过是生活的欲望,生活的本质不过是痛苦,所以只有欲望、生活和痛苦。[14]5
阅读《红楼梦》不难发现,各类人物的悲剧命运往往不是坏人故意造成的,而是大多由于未满足的欲望造成的,如林黛玉对爱情的“来之不易”的苦难,探春对长期婚姻的“爱与分离”的苦难,王熙凤对游二姐的“恨与恨相遇”的苦难等。即使是吃饱喝足的贾宝玉,也“无缘无故地寻找悲伤和仇恨”。这是因为欲望本身是无常的,也就是说,引用“一个欲望就是结束,他想跟随”。即使所有的愿望都得到满足,无聊也会很快发生。这种“欲望”(设定真理)——生活——“痛苦”(痛苦真理)的连锁效应、互动和恶性循环,与佛教对世界因果的认知完全一致。当然,在《红楼梦》中也有“杨飞打蝴蝶”、“偶尔秋海棠俱乐部”等娱乐节目。然而,它们也是短暂的,给整体增添了悲剧性的气氛,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幸福过后,痛苦更深”。这也正如《红楼梦》第一次所言:“红尘中有一些快乐,但不能永远依赖它们。此外,还有“美与中国的缺点、善行和魔法”这几个字是紧密相连的。刹那间,有欢乐也有悲伤,人不会被事物改变。毕竟,这是最后的梦想,一切都将回归空”[13]3因为《红楼梦》反映了人生悲剧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所以被称为“悲剧中的悲剧”[14]12。
尽管《红楼梦》中的悲剧观不同于古希腊的悲剧观,但它恰恰符合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从叔本华的哲学视角定义悲剧艺术:
叔本华认为,悲剧有三种:第一种是由极度邪恶的人和拥有所有能力的人组成的。第二是由于盲目的命运。第三种悲剧的发生是因为剧中人物的地位和关系。没有必要有蛇、蝎子的本性和意想不到的变化,但是普通人和环境迫使它变得更糟。他们知道自己的伤害,把它交出来,交给他们,尽最大努力不让它受到责备。这种悲剧远比前两种更感人。什么事?他表明生活中最大的不幸不是一件例外的事情,而是生活的内在原因。......如果说《红楼梦》,是第三种悲剧。......宝玉对黛玉发誓,但不要对最喜爱的祖母发誓,是共同的道义责任;再说,黛玉是个女人。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黄金和翡翠的结合,木头和石头的分离,蛇和蝎子的出现,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非凡的变化?但是通常的道德,通常的人类情感和通常的环境都在那里。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14]12
在叔本华看来,由恶人的人为或盲目命运造成的悲剧是偶然的或巧合的,所以它不是真正的悲剧。相反,由普通人的无意识行为和在普通情况下造成但无法避免的悲剧,能够真正揭示悲剧的本质和痛苦的根源(相当于佛教的“苦真”和“集体真”)。从这个角度来看,佛教哲学实际上赋予了中国传统悲剧一种和谐的特征,这可以使中西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对悲剧的概念获得一定的共鸣。这也是王国维能够从西方哲学角度解读《红楼梦》的根本原因。当然,佛教赋予悲剧艺术的和谐并不仅限于此。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统一儒道的悲剧观念。例如,佛教的“因果”概念并不违背儒家的教育理念。相反,“善因导致善果”,“恶因导致恶果”因果规律也为儒家的“自虐、自我惩罚、自我悔改、自我解放”的价值观提供了客观依据。[14]9避免了悲剧教育的道德化和僵化,使人们更真诚地接受它。其次,佛教的“因果”概念也为道教超越世俗世界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即通过消除各种消极的心理能量(如贪婪、愤怒、妄想等)来解除痛苦。)在潜意识里。最后,佛教的因果律也统一了儒教入世与道教诞生之间的矛盾,因为根据“因果律”,人们也可以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世俗的解放,即所谓“佛教在这个世界上,不能与这个世界分离”。例如,《桃花扇》中的李项峻、侯方域,《红楼梦》中的甄印石、贾宝玉等人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解放。正是由于上述原因,《桃花扇》、《红楼梦》等深受佛教影响的悲剧作品具有儒、道、释三家融合、中西相通的特点。
四。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在儒、道、释的影响下,中国悲剧艺术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悲剧的理论体系。其中,以“忠、孝、仁、义”为价值取向的儒家音乐教育思想决定了中国悲剧艺术的创作动机和评价标准,形成了一种类型化的“脸谱”表达方式,具有奠基性。道家辩证思维和自然观打破了“悲”与“乐”的二元对立,赋予中国悲剧一种超越性的诞生精神,并赋予其哲学深度。佛教理论通过因果观统一了儒教入世与道教诞生之间的矛盾,从而深化了中国文化对“悲剧”本质的理解——即使没有邪恶的人的创造和命运的无奈,短暂的世俗生活客观上也是一场充满苦难的“悲剧”——即佛教“苦难出道”学说中的“苦真”。由于因果思维揭示了“悲剧”的本质,它成为中国悲剧艺术情节建构的基本逻辑基础。上述悲剧理论不仅在表现手法上,而且在精神内核上都明显不同于西方古典悲观观,不可否认地体现了“悲剧”的内涵和文化特征。鉴于目前对中国悲剧艺术的否定和怀疑大多是从西方悲剧理论的角度出发,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痕迹,构建一套符合中国文化特点的现代悲剧理论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需要,也是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丰富和深化当代世界悲剧理论研究的需要。
参考
[1]王文锦。[《礼记释义》。北京:中华书局,2016。
[2]吴玉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3]论语,大学,中庸[。陈小芬、许宗儒。北京:中华书局,2011。
[4]李雨。临时张贴:插图拷贝[。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8。
[5]程朝祥。悲剧中的人——中西悲剧英雄[比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5)。
[6]谢柏亮。中国悲剧史[。上海:林雪出版社,1993。
[7]张敞。对中国悲剧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4)。
[8]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9]冯大夫。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庄子·[。永芳。北京:中华书局,2010。
[11]何宁。淮南子集解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
[12]汤显祖。汤显祖全集[。焦健徐朔方。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
[13]曹雪芹。《智言斋评石头故事[》。知言斋,评论。北京:线装书公司,2012。
[14]王国维。王国维的文学论述了[的三种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注
1作者注:佛教的“吉弟”不仅指欲望,还指贪婪、仇恨、无知、傲慢、怀疑和嫉妒等所有烦恼的总和。然而,王国维以欲望为代表的《集体论》在这里对此进行了解释。
